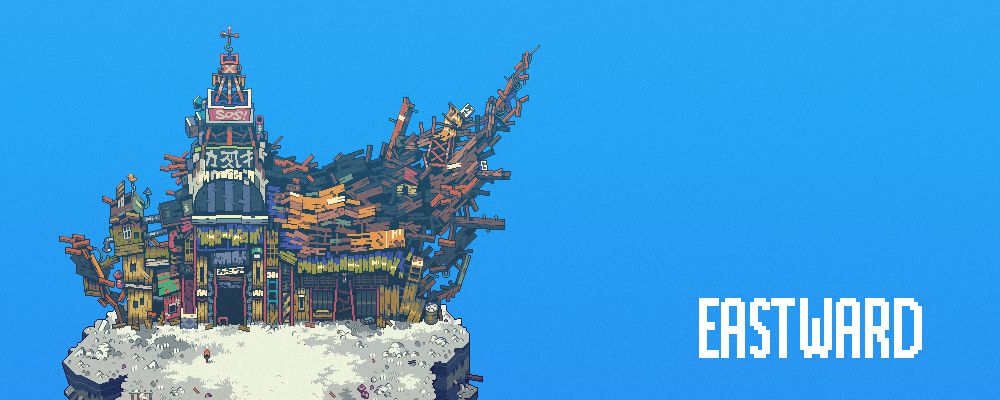刘维开:蒋介石的军事人脉
齐齐哈尔时尚网小编提示,记得把"刘维开:蒋介石的军事人脉"分享给大家!
刘维开
蒋中正在军事方面的人际关系网络,在日记中并不像党、政方面有十分明确的记载,主要原因应该与国民革命军的发展,以及蒋氏与军队的关系有关。
蒋氏早年曾任职粤军,与军事方面原有一定关系,但其日后与军事之网络建立,主要是由于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尔后参与第一次东征,领军第二次东征,奠定他在党内的地位,以1926年之中山舰事件为关键,取得政治的资源。北伐期间透过以黄埔军校师生形成外界所谓之“嫡系”,包括何应钦、王柏龄、钱大钧,以及所谓五虎将即陈诚、蒋鼎文、顾祝同、刘峙、卫立煌等,再向外延伸至其他军系。“嫡系”初期以黄埔军校之教官为主,教官中又以出身保定军校者为多,蒋氏与彼等为同事或长官部属关系,彼等之军中经历、辈分或较蒋氏为高,蒋氏对彼等之态度较为尊重;北伐之后,黄埔前期学生因战功,逐渐升任师、旅长,蒋氏以师生关系扩大影响力;抗战期间,各军、师长由中央军校毕业学生出任者日益增多,至抗战胜利后,中央所能掌控之“嫡系”部队大幅增加,其他军系所占比例相对降低;政府迁台后,经由军队整编,军校毕业生完全掌握国军领导权,蒋氏“国民革命军之父”的地位亦为之确立。
从国民革命军说起
蒋中正被军方尊称为“国民革命军之父”,但是“国民革命军”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军队名称,而是一个类似“联军”的组合,其源于1925年国民政府对所辖军队的整理。
……
“国民革命军”一词,即成为国民政府所属各军的统一名称。
当时由国民政府统辖各军,除陆军军官学校校军扩编而成的党军外,另有建国粤军、建国湘军、建国滇军等。1925年8月初,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建国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建国滇军总司令朱培德、建国攻鄂军总司令程潜等通电,解除各军总司令职务,将所有军队交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率。经多次协商,至8月底大致确定,以党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中正;湘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滇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粤军分为三个军,即第四至第六军,军长分别为许崇智、李福林、李济深。9月20日,国民政府以许崇智“请假赴沪养痾”为由,将粤军整编工作交由蒋氏负责,许氏所遗军长职,由李济深继任,第四及第六两军合并为第四军。1926年1月,军事委员会将攻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以程潜为军长,至此广东全境军队的整编工作大致完成。
1925年9月,国民政府决定对盘踞惠州一带的陈炯明部展开军事行动,是为第二次东征,蒋氏受命为东征军总指挥,开始掌握国民革命军。从组成的过程来看,国民革命军实际上是由各个不同军系组成的联军,蒋氏所能充分掌握者,为其所领导的第一军。1926年1月蒋辞去第一军军长,保举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继任,建立起第一军的传统。其他各军,如第四军由粤军改编而来,蒋氏曾任该军参谋长,并负责许崇智离开后的粤军整编工作,虽然在整编的过程中引起部分粤军的不满,但与该军军、师长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张发奎等有相当关系。李济深更是黄埔军校成立初期的教练部主任,应是蒋除第一军外,较为熟悉的一军。第六军虽成立于第二次东征后,但军长一职系蒋氏致电军事委员会保荐程潜担任,亦应有一定关系。但他与第二、三、五军军、师长关系类似,多属公事上往来,但不见得有私谊,而必须透过不断的接触,建立更进一步的关系。
保定、士官、黄埔
民国以来,陆军的派系复杂,有以领导者的籍贯命名,如北京政府时期的直系、皖系、奉系;亦有以地区命名,如北京政府时期的北洋系,国民政府时期的桂系、晋绥军系、西北军系、东北军系等;亦有以各军事将领毕业的学校命名,如保定系、士官系、黄埔系等。其中以毕业学校命名者,与以领导者籍贯或地区命名者性质不同,属横向区分,其成员包括了各个不同的军系在内。值得注意的是,从蒋中正的军事背景以及经历来看,他与这三个派系都有密切的关系,研究者称蒋氏凭借着与保定系与士官系又培养出庞大的黄埔系,为他的军事发展打下重要的基础。
保定系
保定系是对毕业于北京政府时期陆军部所属陆军军官学校之军系成员的泛称,该校位于当时的直隶省保定,通称为保定军校。军校于1912年10月成立,1923年8月停办,前后共11年,为北京政府时期最主要的陆军军官养成学校,亦是民国建立后第一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蒋中正为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炮科第一期学生,就广义而言,为保定系的成员之一,有称其为保定系中“资格较老的一个”。他在校时间不长,1907年8月入学,是年冬,参加清政府陆军部选派留日学生考试合格,以官费赴日留学。这批考取留学日本的同学,先入留学生预备班学习,然后同往大连乘船前往神户,换乘火车到东京,进入振武学校。蒋氏日后在军政方面的人事运用,有不少人是这批考取留学日本的同学,如黄埔军校筹备时期担任筹备委员、创校初期担任教授部主任的王柏龄及管理部主任林振雄,曾任行政院院长、长期担任蒋氏重要幕僚的张群,曾任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原名杨锦章),创办广西陆军模范营、培植新桂系白崇禧、黄绍竑等的马晓军,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兼典礼局局长张为珊(希骞)等。这批人得到任用应都与曾和蒋一起赴日学习有关,如张群即表示他与蒋氏的结识,是在赴日留学的途中,“一开始便很投契,每每相互畅谈国势,蒋公认为我是可与他兴趣相合的青年”。
士官系
士官系是对于军界中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者的统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培养陆军军官的学校。清政府为建设新式陆军,自1898年开始由各省选派学生赴日本学习陆军。1904年3月,清练兵处奏订《陆军学生游学章程》,明文规定选派学生赴日学习的名额、经费等,并依照章程选派第一批学生108名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嗣后每年皆有由中央或地方政府选派学生赴日学习事,总计自1898年至1911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者有553人,共分8期。民国以后,进入士官学校就读者,持续不断。这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回到中国后,大多进入军界服务,随着时势的发展,跻身领导阶层或成为中坚干部,外界将出身士官学校者,视为一个群体,而称为“士官系”。
蒋中正于1908年以官费赴日,入振武学校。按日本学制,进入士官学校需要接受“军官候选人教育”,为了让中国留日学习军事的学生能进入士官学校,最初是采取由日本陆军省委托一所私立中学成城学校代训的方式,中国留学生先在该校修习军事课程及普通课程,然后接受一年的入伍实习训练,再进入士官学校。之后,清政府与日方协商,决定由日方设立振武学校,作为进入士官学校前的预备学校,负责中国留日学习军事学生教育,1903年正式开办。蒋氏为第十一期学生,学习3年,于1910年毕业,分发至高田陆军野炮兵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见习,预定至1911年12月1日期满,成绩合格进入士官学校就读。不过在见习期满前,辛亥革命发生,蒋氏偕同学张群、陈星枢等未经请假,于10月30日由长崎登轮返国,参加由陈其美所领导的江浙起义行动。日本政府为避免中国留学生受到革命的影响,命令士官学校的中国学生全部退学;同时对蒋氏等脱逃回国,予以退队处分。至1913年,日本政府同意因辛亥革命而未能入学之士官候补生,包括因革命而遭处分者在内,可以进入士官学校,但此时蒋氏投入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并未继续学业。因此严格来说,蒋氏并非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不属于“士官系”;但是因振武学校作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他属于广义的“士官系”。
黄埔系
1924年,蒋氏受任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为其一生事业的关键转折点,尤其在军事方面,随着该校在日后成为中国军界军官的主要培育场所,透过该校师生在军中的发展,得以扩大并强化其在军中的人际网络,成为中国军事上的最具权力的领导者。
陆军军官学校最初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为中国国民党培养革命军干部的军官学校。1924年1月,孙中山正式委派蒋氏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展开筹备工作。5月3日,孙先生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名义特任蒋氏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该校位于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以旧有广东陆军学校与广东海军学校旧址为学校校址,通称“黄埔军校”。1926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国民革命军军事教育有统一之必要,决定改组黄埔军校,合并所辖各军原有各军官学校,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直属该会,并以黄埔军校为校舍,任命蒋氏为校长。1927年4月,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军校随之迁徙,于1928年3月在南京正式成立,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以蒋氏为校长,宗旨在培育陆军初级军官,备充国军干部。抗战期间,该校西迁成都,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1月奉命改名为“陆军军官学校”。1949年12月,成都新政权成立,校务中断,1950年10月,国民党决定以高雄县凤山原第四军官训练班班址为军校校址,陆军军官学校在台复校,迄今已超过一甲子。
蒋氏作为黄埔军校创校的校长,随着其政治地位的提升,对军校的影响力始终存在,特别是前期学生为其担任校长时接受教育训练,与他关系更为密切。自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军队开始倾向私军化,至20世纪初期,军队的派系性、地方性日益严重。国民政府成立后,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是国军中仍然存在各个不同系统,一般多将黄埔系所领导的部队,视为蒋氏嫡系,与其他各军系如西北军系、晋绥军系、桂军、湘军、川军、粤军、滇军、马家军、东北军并列,并以此作为国军中各个不同系统消长的指针。而在所谓“嫡系”军队中,亦有如党、政系统,有派系之分,一般称为抗战后有“陈、胡、汤”,即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大军事集团。
陈诚,保定军校毕业,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向为蒋氏所倚重,蒋于对日抗战初起时曾谓:“军事能代研究者,辞修也。”外界以陈曾任第十一师师长及第十八军军长,称其系统为“土木系”。抗战期间,陈曾任多项党、政要职,并任第九、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远征军司令长官等职;抗战后任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东北行辕主任等;1949年蒋氏下野前,任命其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稳定东南沿海情势。
胡宗南,黄埔第一期毕业,为在黄埔出身将领中升迁速度较快者;1936年出任第一军军长,为黄埔出身第一个升任军长者;1939年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为抗战期间黄埔将领第一个出任集团军总司令者;1945年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为第一个出任战区司令长官者;1945年10月,中将加陆军上将衔,亦为黄埔第一人。
汤恩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事教官,深受蒋氏器重;抗战军兴,率所部第十三军与日军血战南口;后升任第二十军团军团长,参加台儿庄战役,痛歼日军,缔造台儿庄大捷;嗣后曾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等职;抗战胜利后,曾任陆军副总司令,1947年初兼第一兵团司令,率部进攻山东地区共军;1949年蒋氏下野前,任命其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委以守卫上海重任。研究者认为三人所以为蒋氏所重用,有几个共同点:一是对他绝对忠诚,不会对他的错误和不足发表意见;二是均拥有一批由同乡、校友、同僚等关系发展而成的亲信;三是由这些亲信出任军、师长,从而掌控部队。
结拜盟兄弟
蒋中正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结拜盟兄弟。……自《蒋中正日记》对外公布后,根据日记所记,可以明确得知蒋氏的结拜兄弟除了前述的陈英士、黄郛外,尚有邵元冲、朱培德、李宗仁、冯玉祥,其中除邵元冲系在1923年11月访俄期间“订盟”外,朱、李、冯三人均为蒋氏掌握军权后所结交的军系领导人,或可视为经营军中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
朱培德
朱培德,字益之,云南盐兴人,出身滇军,1917年率部加入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成为广东方面的主要武力之一。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后,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任军长。北伐期间,曾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全国统一后,曾任国民政府委员、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训练总监部训练总监等职;1935年4月,国民政府特任陆军一级上将。1937年2月18日,病逝于南京,享年49岁。
蒋氏与朱培德早年虽然同在广东工作,但是并不熟悉,至1925年7月各军改编国民革命军后,方有较密切的往来,并于10月5日换订兰谱,结为兄弟。蒋氏与朱培德结拜一事,未见于任何相关记载,如果不是日记公开,恐怕不会为外界所知。蒋氏并未说明为何与朱培德结拜,但是就时间点来看,应该与处置熊克武一事有关。熊为川军将领,所部驻于北江一带,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为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党内资历颇深。10月1日,陈炯明派人游说朱培德加入其阵营,并表示陈与熊早有约定,只待朱的同意。朱培德大怒,下令将来人拘捕,并报告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得知后,经查证又发现新的证据,觉得事机危迫,于3日将熊克武扣押,是为“熊克武事件”。在此事件中,朱培德的态度实为关键。在此之前,蒋氏对朱即颇有好感,8月14日,蒋氏与朱培德谈话后,记道:“下午朱益之军长来谈。此人诚一血心男子,可与共事也。”而蒋与朱于10月5日结拜,系在熊克武事件后第二日,不能不联想两者的关系,又据所记:“晚……又访朱益之,与之换订兰谱。”此事应为蒋氏主动。
朱培德与蒋氏的关系大致良好,学者认为朱对蒋的服从,“更多的是把蒋当成是国民党或国民政府的象征”,蒋氏亦颇为信任朱培德,自1932年3月起请其担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至1937年2月病逝,前后长达5年,协助处理会内日常事务,并参与抗日战争的准备工作,可以说是蒋氏在军事方面十分倚重的幕僚。学者表示“以往观念是,蒋介石只信任和重用嫡系,对于非嫡系,往往加以排斥,但朱培德非蒋的嫡系,却深受蒋的重视”,但是从两人结拜以及朱对蒋氏的服从来看,恐怕不能以“嫡系”或“非嫡系”的观点来说明蒋氏重视朱培德的原因。另一方面,蒋氏对于朱的个性虽然有消极、守成、无勇气等批评,但是却十分肯定他的才能,认为朱是政府官员中的贤才、干才。
1937年2月,朱培德因风寒注射针剂,引发败血症,于17日晨6时入住南京鼓楼医院医治,蒋氏得知讯息后,立即前往探视,嘱其安心住院休养,未料至晚上10时病情急剧恶化,延至11时20分病逝。蒋氏于17日日记记道:“下午甚念益之,此时并未知其有病也。下午六时,闻其病重之报,乃即驱车往视,其神志甚清,觉未如医生所言之剧也,此心尚安。及至十一时后,余正欲移院,因促余妻回来,不欲余前往,恐病中生感,但其并未言益之已于十一时彼回时已死也。及至今晨醒后,妻方告余以益之昨夜之死耗,不胜悲哀之至,所部又弱一个矣。”复感慨记道:“益之逝世,又缺一个智勇精诚之同志。近年来得力于益之无形之补助,殊非浅鲜。益之在军委会苦心孤诣之主持,代余调理一切,今后再无其人矣。”以后数日,18日亲往吊唁;19日赴停灵之仁孝殡仪馆视察治丧相关事务;20日,朱培德遗体大殓,亲临主祭,记道:“下午,益之大殓,观其遗容不胜悲伤,侪辈之丧,以益之为最痛也。”21日,朱氏灵柩移往毘卢寺,亲往迎灵,并主持安灵礼。及至22日日记“注意”项下,仍记有“益之丧仪”等字,相较于其他党国要员,蒋氏对朱培德生前死后之重视程度,是极其少见的,亦可知其对朱培德逝世所承受之悲痛,正如他在当月反省录记道:“益之逝世为今年最大之损失。”是年底,南京遭日军攻陷,政府移驻重庆,12月31日,蒋氏记事忆及朱培德,曰:“去年今日犹在南京与益之、天翼等密商大局也,未知明年今日将如何耶?”翌(1938)年1月16日,蒋氏于上、下午接见将领,看土耳其革命史,“自觉智慧学识之欠缺,忍心耐力之不足,所以遭此困阨也”,想起朱培德生前对他的协助,曰:“无骄不败,最缺诤友与谋士,如益之不死,则战祸或可减少也。”或许更可以看出蒋氏对朱培德之态度。
李宗仁
李宗仁,字德邻,为桂系领导人之一。1926年初与白崇禧等率广西部队加入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于3月15日通过两广统一案。24日,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李氏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两广统一。蒋氏于1926年8月10日与李宗仁结拜,距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满一个月,正在往长沙途中,抵达衡阳。据当日蒋氏日记:“李德邻军长来谈甚久,乃知孟潇一决心革命,可喜可贺。下午与夏曦谈天,李德邻谈天甚久,德邻为一血心之军人也,与之订盟。休息。” “孟潇”为唐生智。其中“血心”两字与对朱培德之评价相同,或许这即是蒋氏与人结拜的原因,而就蒋氏所记,应是主动寻求“订盟”。
《李宗仁回忆录》中亦记有此事,虽然未注明结拜的时间,地点亦将衡阳误作长沙,不若蒋氏日记精确,但记述较为详细,可以参考。谓:
在长沙时,还有一趣事值得一提的,便是蒋总司令和我“桃园结义”的故事。蒋氏到长沙后,我时常在总司令部出入,有时是有公事接洽,有时却是闲谈。我去见蒋总司令也毋需预先约定。一日,我在蒋先生的办公室内闲话,他坐在他的办公桌椅子上,我却坐在他的桌子旁边一张木椅上。蒋亲切地问我说:“你今年几岁了?”我说:“三十七岁。”蒋说:“我大你四岁,我要和你换帖。”所谓换帖,便是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我念头一转,心想蒋先生为什么来这一套封建的玩意儿呢?令我不解。
我说:“我是你的部下,我不敢当啊!同时我们革命也不应该再讲旧的那一套啊!”
蒋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必客气。我们革命,和中国旧传统并不冲突。换帖子后,使我们更能亲如骨肉。”
他说着便打开抽屉,取出一份红纸写的兰谱来,原来他已经事先填写好了要我收下。我站起来说:“我惭愧得很,实在不敢当。”坚决不收。蒋先生也站起来说:“你不要客气,你人好,你很能干……”我一面回话,一面向后退,表示不敢接受他的兰谱。他抢上两步,硬把他的兰谱塞入我的军服口袋里。并一再叮嘱我也写一份给他,弄得我非常尴尬。
辞出之后,我拿蒋先生所写的兰谱看看。那上面除一般兰谱上所共有的生辰八字和一般如兄如弟的一类例有的文字之外,还有蒋先生自己所撰的四句誓词,文曰: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德生死系之誓词之后除“蒋中正”三字的签名之外,还附有“妻陈洁如”四字。看后我便想到,蒋先生搞这一套封建时代的玩意儿,其真正目的只不过是拉拢私人关系,希望我向他个人效忠而已,其动机极不光明。我想当时南北双方的要人,相互拜把,或结为亲家的正不知有多少,但是往往今朝结为兄弟,明日又互相砍杀,事例之多不胜枚举。反观我们广西的李、黄、白三人,并未金兰结盟,而我们意气相投,大公无私的合作,国内一时无两。相形之下,益觉以封建手腕作政治结合的方式有欠正派。蒋总司令在当时是炙手可热的领袖,能和蒋氏结拜兄弟,任何人都必然要受宠若惊。然而我的心里却老大的不高兴,所以除内子一人知道之外,我未向外间任何人提及此事。
就李宗仁所回忆,结拜一事确实是蒋氏主动,而他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才与蒋氏交换兰谱。不过就蒋氏此一时期日记所记,他在此时与李氏互动频繁,印象十分良好,如8月28日与李氏谈话后,记道:“下午李德邻军长来谈,甚乐。”而李氏与蒋谈话时间颇长,蒋在日记中多次有“李德邻来谈甚久”字样,亦可见李宗仁此时对蒋氏亦十分友善,两人关系生变,应与1927年蒋氏下野有关,而回忆录为日后所记,难免与当时情形有所出入。
冯玉祥
冯玉祥,字焕章,原属北洋系中的直系,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倒戈,推倒直系所控制的北京政府,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926年1月在奉、直两系联合进攻下,失败下野,旋赴苏联考察。是年9月,冯氏召集旧部于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全军加入中国国民党,响应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年5月,接受武汉国民政府任命,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总司令;随即于6月分别与武汉国民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要员会议于郑州、徐州,而在徐州与南京国民政府要员的会议,第一次与蒋氏见面。6月19日,蒋氏亲自在徐州车站迎接冯氏,随即会议。当日,蒋氏于日记记道对冯之印象“老练沉着,心实钦佩,自惭轻浮,时觉惶恐”,“甚想以总司令名义交焕章同志任之,余独负训练之责也”。 1928年初,国民政府决定展开第二期北伐,2月16日,蒋氏抵开封与冯玉祥会商第二期北伐计划,17日下午到郑州出席军民欢迎会,随后往郊外考察农村,蒋、冯结拜即在此时。据蒋氏当日日记:“下午到郑州欢迎会,后往郊外参观农村,焕章欲约为兄弟,乃换兰谱,八时由郑州出发。”“焕章欲约兄弟,乃换兰谱。”蒋氏之《事略稿本》记载更为详细,曰:“下午赴郑州,郑州军民开会迎公,公答谢已。又往郊外,考察农村状况,冯玉祥终日随行,勤勤恳恳,请与公为兄弟之盟。公曰:吾人同力一志,为国为民,义同死生,情自兄弟,盟与不盟,其实一也。兄今欲盟,亦无不可,遂与为盟焉,冯氏大喜。晚八时,公去郑返徐,冯氏送至开封乃别。”由蒋氏日记及《事略稿本》来看,结拜一事为冯氏所提出,蒋氏实处于被动。”
结语
综合而言,军队本身是一个层级严密的组织,上下关系十分清楚,对于上级的命令要求绝对服从,蒋中正从黄埔军校校长开始,在军事方面长时期居于领导者的地位,除了与各个不同军系领导者之间需要维持友好关系,以便于运用各军系掌控的部队外,与各个军事将领间,长期处于长官与部属或校长与学生的关系,公谊多于私情,其人际关系实不如党、政方面明显。
革命 抗战 日本